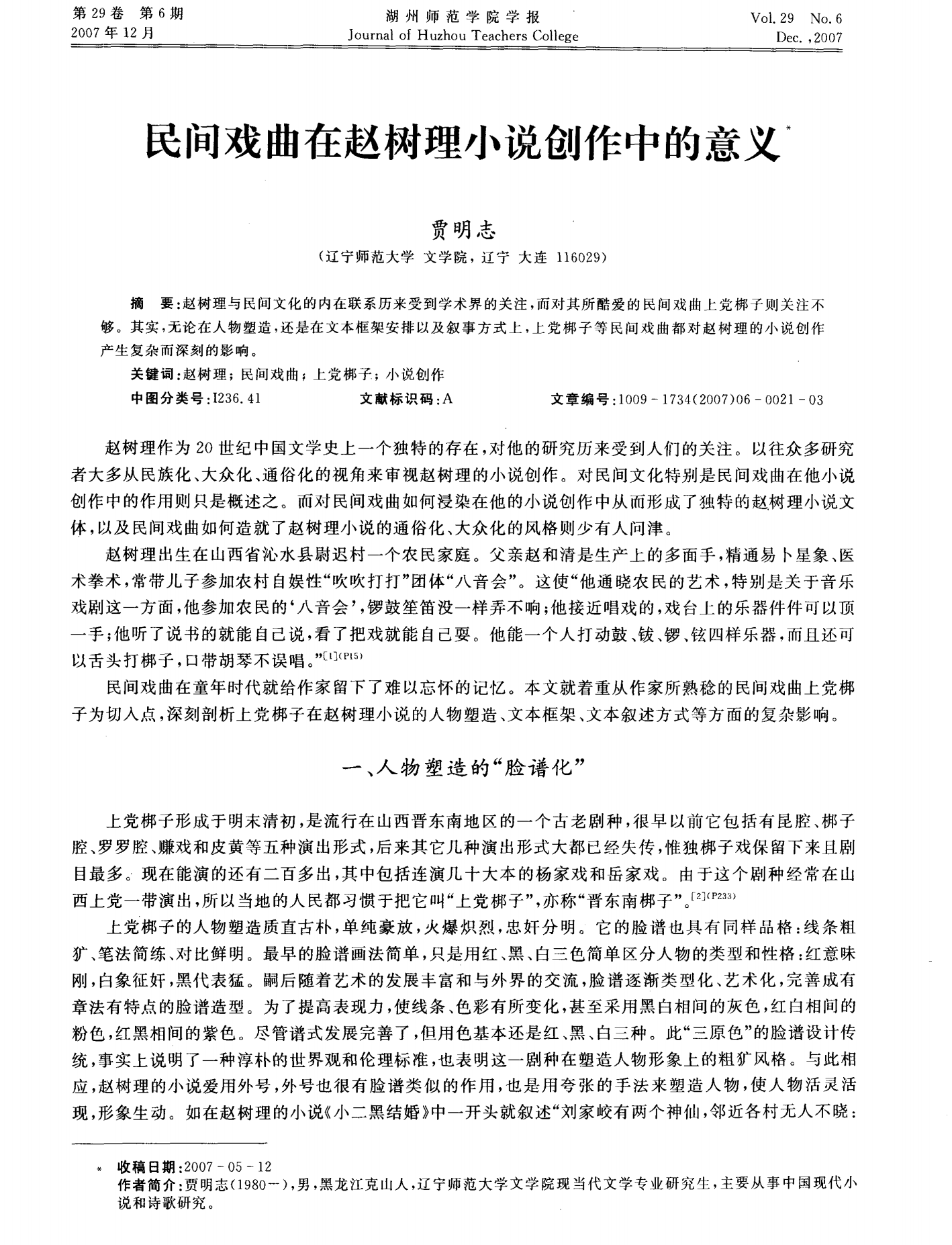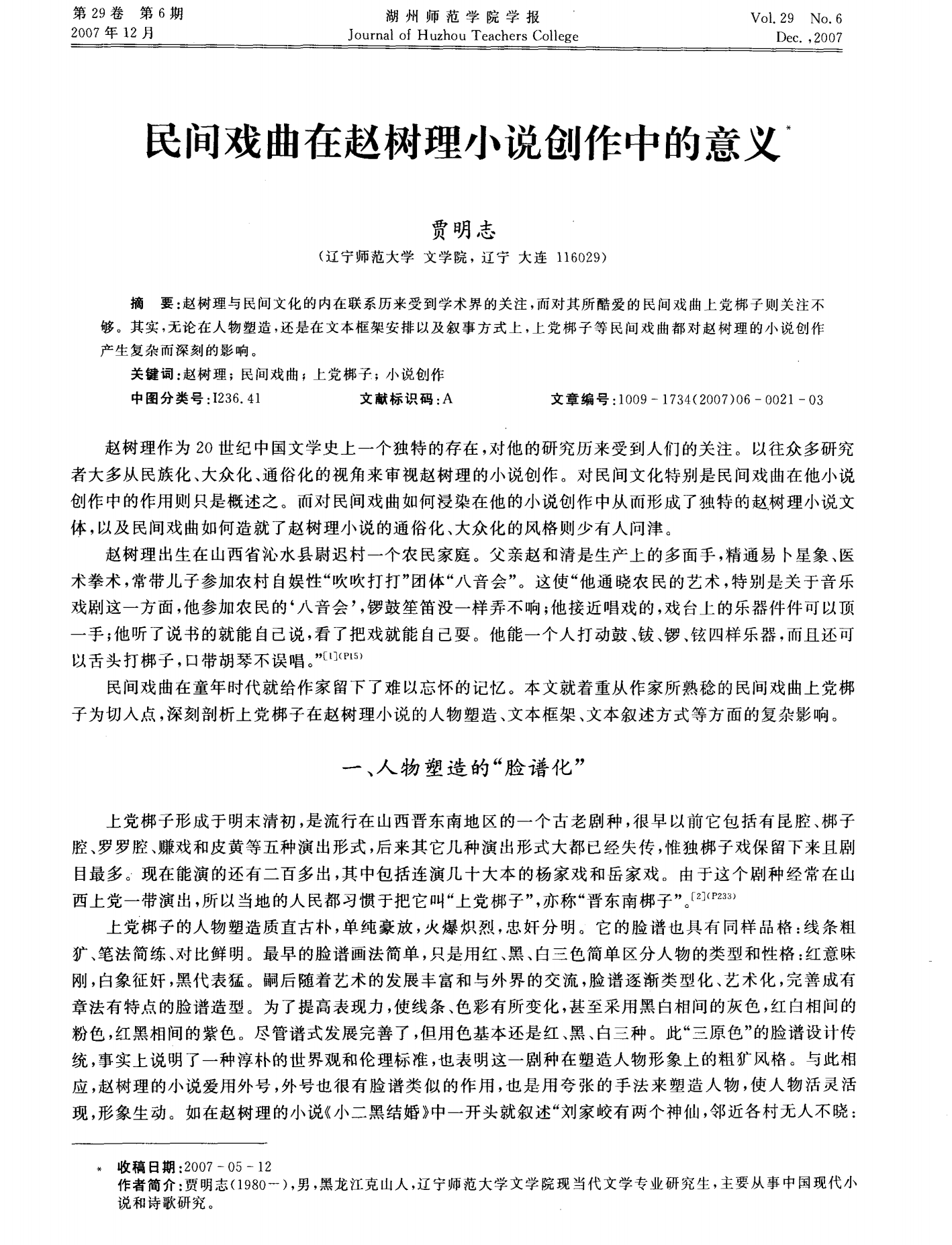预览加载中,请您耐心等待几秒...
预览加载中,请您耐心等待几秒...

1/8

2/8

3/8

4/8

5/8

6/8

7/8

8/8
在线预览结束,喜欢就下载吧,查找使用更方便
如果您无法下载资料,请参考说明:
1、部分资料下载需要金币,请确保您的账户上有足够的金币
2、已购买过的文档,再次下载不重复扣费
3、资料包下载后请先用软件解压,在使用对应软件打开
赵树理文学史意义_赵树理文化建构对当下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摘要:服务农民,为农民书写,是赵树理创作的旨归。抱着这种理想的赵树理,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捍卫农民切身利益写“问题小说”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赵树理执着的理想就是站在农民的一旁,为民所想,为民所做,建设和谐乡村文化。这种为民请命为民服务的执着也使得赵树理及其文化建构对当下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意义。关键词:赵树理;文化建构;新农村建设;问题小说;启蒙“新农村建设”关系到当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代作家如何在新的文化交替转折过程中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把自我融入到伟大的农村建设中,继承传统乡土文化精神,写出更多的力作和精品,是当代文学期待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此,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书写姿态和执着,秉承着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建设和谐乡村文化,为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成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一、农民代言人的姿态——“问题小说”的“现实”指导意义贺仲明在《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一文中,把20世纪乡土小说分为四种创作形态,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形态;以茅盾为中坚的政治功利形态;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明怀旧形态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代言形态。不同于前三种的乡村代言形态的作家们选择的是乡村自身的立场,他们代表着乡村人或乡村文化的利益,从内部来观看和书写乡村世界。[1]如果说鲁迅、茅盾、沈从文是以先知先觉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农民启蒙,赵树理则是以朋友的身份与农民拉平了关系。正是这种平等的关系,加上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使得他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显得具体而实在,因而乡土味更浓,乡土人民的生活描写更加深入。所以从“现代性”的意义上讲,鲁迅所关注的是礼教对国民灵魂的禁锢,赵树理所关注的是习俗、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囿限。赵树理从现实功利的“问题”切入,“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2]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是一种渗透着赵树理深深地关爱农民的意识和为民忧患的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具有能虚心向下,正真地为民办实事说实话示范作用,对农民由拆迁、进城打工遭遇的深层次物质转换及心理变化问题提供新的体验角度,对社会转型中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性”是研究者的一种表述,他的小说的确在民族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社会政治教育作用的功效,然而,我们应该探究赵树理这些“问题”的真正创作动机的趋向是什么。有一段赵树理的自述,研究者喜欢引用作为论据:“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英雄报道之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情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意义”[3]。赵树理的“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的“问题”,正如席扬先生所说,是赵树理捕捉到的农村及农民生活中现实“生存困境”的“问题”。农民“生存困境”的“问题”不是单单具有政治方面的含义,而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问题。[4]赵树理的大部分作品是从此处着手描写。如看到“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的地主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人多,老杨式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5]的《李有才板话》。再如《邪不压正》,赵树理创作意图是引起土改干部注意土改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他则写的是“一个流氓趁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因为这些乘机窃权的“流氓”不引起警惕,将会给农民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后果。显然,这些“问题”选择的“生存困境”意味,是赵树理“农民代言人”的体现者对“百姓大众”理性思考发现的归宿。在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新旧交替时期,新与旧,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将变的异常尖锐激烈,能不能及时发现新的问题,能不能妥善解决新的问题,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新旧力量孰胜孰败的较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赵树理积极投身其中,显示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从30年代赵树理产生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志愿,到他“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只要群众看的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6]的决心,再到他“说书唱戏是劝人哩!”不仅“不是为劝人”“就可以不写”,而且“劝人”[7]的意义不大,他也不主张写的现实实际功利目的,以致在50年代作为一个解放后被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